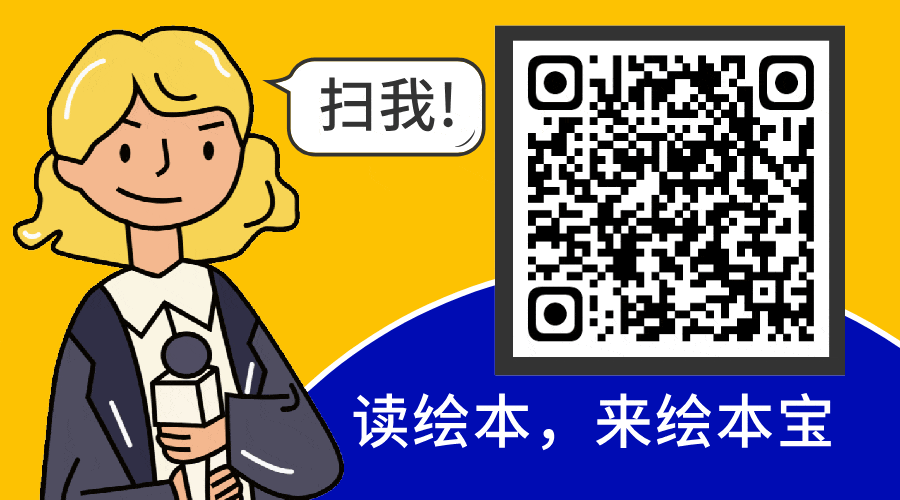

上海滩虽已沦陷,日本兵扛着三八大盖在马路上巡逻,枪刺在阳光下闪着冷光,但那些有钱人照样过着灯红酒绿的生活,甚至有些工商巨头还跟日本人打得十分火热,合资开店办厂。老百姓对他们狠之入骨,背地里骂他们是奸商。此“奸”有两重意思,一是刁滑;二是汉奸。黄昌荣便是其中一个,他在杨树浦开了两家纱厂,一家钢铁厂,不但日本人是股东,连大板和拿摩温都用的是日本人,他们对工人凶狠残暴,不是打就是骂,尤其无视人的庄严,对出厂的纱厂女工进行搜身。大家背地里叫黄荣昌“二鬼子”。

可能黄荣昌作恶太多的缘故,他的一妻二妾都没给他留下一子半女,至今屁股前面光溜溜。最近他又娶了第三房妾,叫方茹珍,是在大世界唱本滩的。黄荣唱喜欢本滩,常常在家哼上几句,每周必有一个晚上去观本滩过过瘾,看上了长得漂亮的方茹珍,把她娶回了家。
但过了半年,方茹珍的肚子也是瘪塌塌!黄荣昌这才意识到毛病出在自己身上。这个死不要脸的家伙竟对方茹珍明说:“你给我到外面去找个野男人,若得子息,我赏你一座纱厂!”方茹珍听了自然欢乐:“你说话可要算数。”“正人一言既出驷马难追。”黄昌荣拍着胸脯说,“不过你得找个长相俊一点的。”“这个不用你吩咐,我方茹珍这么漂亮,怎么会去找个丑八怪?”
方茹珍是个唱戏的,感情自然丰厚,心里早有了念头——也要找个唱戏的!
戏子不仅人俊,且大多情种。于是她险些天天晚上去大世界,从这个舞台到那个舞台,一双丹凤眼瞄向那些俊逸的小生。
南京来的一家京剧团在大世界挂牌上演《西厢》,连演十场场场客满!观众们都说,“小胡蝶(butterfly)”把天真热情聪明机警的红娘演活了!另有那个演张生的英鹏,眉眼里都是情,且貌若潘安,台下那些太太小姐一个又一个被他迷了心窍。方茹珍暗下说:若能跟他睡一晚死了也甘心!
大世界不是高档戏院没有包厢,要占到一个好位子看夜戏必早去才成,方茹珍不等午场散了便去,身上带着糕点充饥。为了讨好英鹏,她每晚都买了一个大花篮送到背景,从不留名。一晚她心花怒放,竟在英鹏谢幕时,脱下手上的一枚金戒指扔了上去,嘴里喊着:“接了——”戒指不偏不倚砸在英鹏头上,引得台下一片笑声。英鹏一双情眼朝发声的地方望去,和她的目光相遇,不由都放了电。
终于有一晚,她让车夫把车停在大世界边门,等待英鹏出来。当卸了妆的英鹏走来时,她迎了上去,学着戏里的红娘道:“张生,你随我而来。”英鹏知趣地作一揖:“多谢红娘姐——”她殷勤地邀他上车,载他去新雅饭店,请他吃了夜宵。这样几晚后两人都生了爱意。方茹珍不能带他去黄公馆,便和他在外面开了房间。两人似胶似漆地过了一宵。
有了第一晚,必定有第二、第三晚,方茹珍和英鹏一再幽会,不久便暗结珠胎。方茹珍忙把这喜讯通知丈夫。黄昌荣喜出望外,夸她说:“茹珍,你是我们黄家的大功臣哪!但愿生个男孩就好啦。”“我生了男孩你可不能忘了你说过的话。”“我怎么能忘记呢?生了男孩一定赏你一家纱厂。”他保证说,“母以子为贵嘛,自古以来都这样。不过,你不能再跟那个小白脸戏子来往了。”“那当然。”她口里虽答应着,心里却打着另外的算盘:我怎么舍得跟他合并?就是丢下孩子也要和他远走高飞!
十月妊娠一朝分娩。方茹珍真产下了一个男婴!喜得黄昌荣直念阿弥陀佛:“看来我黄家前辈子一定积了福,所以老天爷赏我一个儿子。”方茹珍对黄昌荣说:“你现在可以实现你的诺言了罢?”他马上说:“好好,我明天就把一家纱厂的一切股份转到你的帐上。”方茹珍偷偷把这喜讯通知英鹏。两人便做着把纱厂的股份一切卖掉,随后回英鹏老家的美梦。他们哪里知道此时黄昌荣正酝酿着一个恶毒的阴谋!
这天黄荣昌笑嘻嘻对方茹珍说:“茹珍哪,那个戏子小白脸叫什么来着?”“你问他姓名干啥?”她小心地问。“你误会了,我没有一点恶意,我黄昌荣不是无情无义之辈。不管怎么说,没有他我哪来的儿子?我想请他吃顿饭,好好背后谢谢他,打算给他一笔钱。”听他这么说,她提着的心放了下来,把事儿通知了英鹏。英鹏也没往弊端想,次日正午便来黄公馆赴宴了。
黄昌荣没请别人,就自己和英鹏两个,叫下人到饭馆订了一桌酒菜送来,摆在公馆后花园里。这花园虽不大,却假山池水,亭台楼阁,曲径长廊一应齐全。
他让车夫用自己的雪铁龙车把英鹏接来,邀他到后花园入座。
女侠除奸记(2)
他给英鹏斟满酒:“英鹏先生,你劳苦功高,我先敬你一杯。”英鹏把酒挡回去:“很抱歉,黄老板,我从不饮酒,再说晚上还要唱戏。”黄昌荣咧嘴一笑:“好,好,那就吃菜,吃菜。”他用筷子指指桌上的菜。两人吃了一会,黄昌荣说:“这样干吃没意思,我请人来娱乐娱乐。”言罢击了三下掌。只见从假山后走出两个扎着头巾的日本武士。
英鹏一惊,忙起身抱拳:“黄老板,如果没啥事儿的话我就告辞了。”说罢也不管他答应不答应,转身就走,到门口却见铁门早已关死!“嘿嘿``````”黄荣昌一阵冷笑:“来了就别想走——”说着朝两个武士一努嘴。英鹏虽是演小生的,但也会一点拳脚功夫,知道来者不善,便把后背往墙上一靠,摆开架式。
“你的过来!”一个武士朝他招招手,另一个狞笑着:“我们的一对一的较量。”英鹏知道自己上了当,怒斥黄昌荣:“好你一个卑鄙小人,二鬼子,竟然做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来。”黄昌荣又一阵冷笑:“嘿嘿``````伤天害理的不是别人,是你——勾引我三姨太,给我戴了一年多的绿帽子。明天若留着你,我黄昌荣就见不得人。再说这男孩总是你的骨血,以后麻烦事的事儿多着呢!”说着一挥手,两个武士便凶狠地朝英鹏扑了已往。
英鹏怎敌得过两个似虎似狼(wolf)、墩实力壮的日本武士?不一会儿便被打翻在地。他们把他拖起来,把他当沙袋般击已往踢过来。英鹏脸上身上全是血,简直成为一个血人。见他奄奄一息,黄昌荣指指假山:“把他拖到下面地窖里,冻死他!”两个武士便将英鹏拖走了。一会儿他们上来,用木桶舀池水将地上的血迹冲洗干净。黄昌荣赏了他们每人十块大洋,打发他们走了。
眼看戏就要开场,可英鹏还没有来!班主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ant)团团转,问小胡蝶,小胡蝶只得实话实说:“他去黄公馆了。”班主听了“啊呀”一声,“英鹏怎么不听我的话?这黄昌荣是个人面兽心的家伙,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他给黄昌荣戴了绿帽子,黄昌荣会放过他?”小胡蝶说:“我也劝他别去,可他不听,说他给黄昌荣生了个儿子,黄昌荣感激他还来不及呢!”“糊涂!”班主跺着脚,“他现在还不来,八成是出事了!好,也不管他了,依然救场要紧,可谁能顶他的角呢?”“叫我师姐顶吧。”“你师姐?”班主不相信地,“她可从没演太小生,再说这些年她没唱戏,行吗?”“怎么不行?”小胡蝶把握十足说,“她来上海已经十多天了,天天坐在背景看戏,熟得背都背出来了。”班主不再犹豫:“也只能这样了。那就叫她快化妆吧。”
小胡蝶的师姐叫杜鹃(cuckoo),江湖上人称“檐上飞”,可见她轻功了得!原来也是唱戏的,后因受地方上恶霸的欺侮,一怒之下便习了武,在江湖上仗义行侠,因在皖北犯案官府缉拿,故来上海躲避。她受师妹之托化妆后登台,想不到演的还不错,观众认可他这个“张生”,掌声热烈。翌日英鹏依然没有来,班主只得到外面去借人顶他。
第三天英鹏仍毫无踪影,班主便和大家商量说:“英鹏去黄公馆已整整三日,至今尚未返来,看来是凶多吉少。我想请人设法去打探,务必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大家一致赞许。可请谁去呢?又是小胡蝶推荐:“请我师姐去吧,她武艺高强,别说是黄公馆,就是巡捕房也能轻松自如地进出。”杜鹃爽快地一口答应:“决不辜负大家的重托!”至晚,杜鹃换上一身玄色夜行服,背插短刀,怀揣飞镖,戴上头套,蹬上便靴,“嗖”地上了房顶,像一只飞燕朝黄公馆方向而去。
三姨太方茹珍,那天正午在房中坐立不安,盼望英鹏能见上他们的小宝宝一面。她频频去后花园,可都是“铁将军”把门。终于盼到房门响,走来的却是自己的丈夫!“他人呢?”她迫不及待问。“送他走了。”黄昌荣面不改色,“还赠了他一百块大洋。”“真的?”“我骗你干吗?我黄昌荣是懂得知恩图报的。不过你们就到此为止,再也不要藕断丝连了。”他有啥介事说。“这个当然。”她笑着答应,心里却在说:等纱厂到手后叫你跳断脚!
杜鹃进了黄公馆,首先寻找三姨太的住处,认为她知道英鹏的下落。可三姨太住哪儿呢?杜鹃侧耳谛听,一阵婴儿的啼哭声传来,便循声找去。她一个倒挂金钟身子从屋檐上悬下,从窗口望出来,见只有三姨太一个人,便翻身下来,“笃!笃!”她敲了敲门。
“谁呀?”方茹珍问。“我。”杜鹃压低声音,“英鹏。”她信以为真忙走来开门。一见是个夜行人,她吓得一声尖叫。杜鹃忙掩住她嘴:“嘘——我是来寻找英鹏的。”“他、他不是回、回去了吗?”方茹珍唬得舌头打结。杜鹃摇摇头:“他已经三天没回戏班了。”“啊——”方茹珍大惊失色,“那我丈夫怎么说送他回去了?还说赠了他一百块大洋。”“你信吗?”杜鹃问。她不知可否地望着杜鹃。“黄昌荣在什么地方宴请英鹏?”“后花园。”“请你带路。”她望望熟睡的儿子,说“好”。
方茹珍在前面带路,止不住身子一阵阵颤抖。杜鹃问:“你冷?”“不,我、我怕。”她牙齿“咯噔噔”地打着颤。“怕什么?”杜鹃又问。“我总觉得不太对劲。后花园从来不锁门,那天却锁了。”“噢——你听到什么动静没有?”她摇摇头,“因我怕儿子醒来,所以站一会儿就回去了。”
花园的门洞开着,晚上也没锁,可见方茹珍的畏惧不是没有道理。进了门杜鹃仔细察看四周,在假山前蹲下身子,用手电照着。她看到地上有一些草半卧在地上,显而易见有物体在上面压过,如果分量不重,草早就竖起来了,那是什么物体呢?见倒伏的草距离较长,便大胆判断那是人!突然之间她发现一棵草的叶端呈白色,便拔下放到鼻子下,闻到有股血腥味,更加断定是人,想八成英鹏被害了!
她走到假山边,用手电照着。方茹珍突然之间之间之间忆起说:“假山下有个地窖,那是为躲避飞机扔炸弹而挖的。”“在哪里?”杜鹃问。“那头有个盖子。”方茹珍指着说。杜鹃便走了已往,果然那里有个约三尺见方的盖子。她弯下腰,手扣住盖耳,一使劲盖子便开了,用手电一照,有台阶,便走了下去。
女侠除奸记(3)
下面一无所有,又潮又冷,杜鹃不由打了个寒战。她欲转身离去,却闻到一股浓烈的血腥味,便走到底下,用手电照看,看法上有滩殷红的血水!看来黄昌荣陷害了英鹏后将他拖到地窖,之后又把尸体转移或毁了。她又仔细察看了一下,见阶梯边有个发亮的东西,拿起一看竟是个铜扣子,便捡了起来。
见她上来,方茹珍问:“你看到什么了?”杜鹃把扣子给她看:“你熟悉这东西吗?”方茹珍看了惊叫起来:“这是英鹏衣服上的扣子,我帮他缝过。”顿时她被一种不祥的预兆攫住:“难、难道他、他``````”杜鹃神色凝重地点摇头:“英鹏他遇害了。”“啊——”她支撑不住身子往后倒去。杜鹃忙一把扶住她:“这里不是久留之地,依然回你房里说话。”
回到房里方茹珍失声痛哭。杜鹃忙劝住她:“不能大声,万一被黄昌荣知晓,你的性命也难保。”这时床上的婴儿醒了,“哇哇”地哭着。方茹珍忙将他抱起,跟他一路哭了起来:“呜``````苦命的孩子,你知道吗——你出生还不到一个月,你亲爹他、他就被恶人害了!呜``````”她把那个铜扣子放到桌上,抱着儿子膜拜:“英鹏,你在天之灵一定要保佑我们母子平安,等儿子长大了一定要他为你报仇雪耻。”见她抽抽噎噎泪水长流,杜鹃义愤填膺:“等你儿子长大要到什么时候?倒不如让我出手将这狗汉奸除了!”
听她这么说,方茹珍忙转身朝她磕头:“多谢义侠鼎力相助,我方茹珍和儿子永久不忘,定为你塑尊金像,天天膜拜。这狗汉奸黄昌荣,卖国求荣,把棉纱给日本人做军需品,把钢铁给日本人造枪炮,他的罪恶罄竹难书!”杜鹃赞许地点摇头:“他罪有应得,死有余辜。”她扶方茹珍起来:“让我们好好商讨一下,怎样能既秘密又干净地将他除了?”
这晚,方茹珍打电话到纱厂,骗黄昌荣说:“老爷,儿子病了,不肯吃奶,只是‘嗷嗷’地哭。”黄昌荣一听急了,忙说:“好,我马上返来。”半小时后,他性急沉着地返来了,才踏进一只脚便大声问:“茹珍,儿子怎么了?马上送医院,车夫在下面等着呢。”
“不用送医院。”一个陌生的声音说。他刚想转头,只觉脖子上凉嗖嗖的,低头一看,一把明晃晃的刀架着呢!霎时他唬得两腿像筛了糠般抖个不停。“坐下!”一声严厉的断喝。“是,是。”他乖乖地在椅子上坐下。他这才看清,面前屋里站着一个着一身黑蒙着脸的人,听声音是个女的。“女、女侠饶命,要钱我、我马上给你。”他忙请求。“谁要你的臭钱?”杜鹃将刀动了动。“那、那就金、金条吧。”“也不要你金条。”“那、那你要、要什么?”“要你的狗命!”他一听吓得身子一软滑倒在地上。
杜鹃朝方茹珍使个眼色,她马上到窗口大声对下面的车夫说:“阿发,少爷不用送医院,你去歇息吧。”“嗳。”阿发答应一声把车开走了。“女、女侠,我和你无冤无仇,你为、为何``````”“你这汉奸,和全中国人民都有仇!”杜鹃打断他话说,“我问你——英鹏可是你害死的?”“我、我没、没有。”“哼,你还想承认?”杜鹃将刀轻轻一抽,他脖子上立即有个口子,血淌了下来。“好,我说,我说!英鹏是我害死的。”
“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方茹珍要朝他扑去,被杜鹃拦住:“咱们到后花园去审他。起来,走——”她用刀逼着黄昌荣。黄昌荣被押着朝后花园走去。
到了那里,杜鹃问:“英鹏是怎么死的?”“是、是被两个日、日本武士打死的。”“你想推卸责任?哼,不是你去请,他们会来吗?”“我、我有罪。”“你又把英鹏拖到了地窖里是吗?”“是,是。”
“你、你这么怎么毒辣啊——是你要我去找野汉的,怎么能把人家杀了?”方茹珍又朝黄昌荣扑去,再次被杜鹃拦住:“别再跟他噜嗦,让他见阎王得了!”说罢她手一举一挥,只见一道白光闪过,黄昌荣没哼一声便像一只重重的的粮袋倒了下去。杜鹃把刀在他衣服上擦了擦,随后插在身后,又将一张早已写好的纸条丢在他身上。
为了不牵涉到方茹珍,杜鹃回到她房里,将她绑在椅子上,随后看护说:“等我走了半小时,你就呼唤招呼下人来救你。”“嗳。”她答应着,“女侠,请留下你的姓名,日后我可以报答你。”“杜鹃摇摇头:“我不图报答,只想除暴安民。昔日杀了大汉奸黄昌荣,必定大快人心。黄昌荣死了,你留在这里另有什么意思?再说他另有几个女人,她们一定会妒嫉你,我看你依然远走高飞吧。”方茹珍连连摇头:“你说的对。我一定离开这个鬼地方,回自己故乡去。”
半小时后方茹珍大喊“救命”,下人们闻声赶来将她松了绑。“老爷呢?”下人问。她摇摇头,拍着胸脯:“吓死我了,吓死我了。那黑衣人把刀架在老爷脖子上将他押走了。”因为这里是法租界,所以他们向法国巡捕房报了案。巡捕很快来了,在后花园发现了黄昌荣的尸体,尸体身上有张纸,上书:狗汉奸的可耻下场!
第二天《申报》头版头条刊登了一条新闻——工商巨头黄昌荣死于非命。
女侠除奸记(4)
大汉奸黄荣昌死了,他的那些厂子被日本人夺去,黄公馆里也是树倒猢狲散,他的那些女人和下人都拼命抢资产。方茹珍带着个孩子怎么抢得过人家,幸亏她多了个心眼平时把钱都存在银行里,够她过好些年的。趁乱之际,她带上自己行李抱上儿子静静从后门出去,叫上一辆人力车离开了黄公馆。
她没有落脚处,便在旧弄堂里借所房子暂且安顿下来。她是个享受惯的人,所以请了个保姆帮助带孩子,自己则腾出身子出去找工作。是啊,再多的钱也会坐吃山空!她留下儿子是想将来靠他养老。可到哪里去寻活干呢?她自然而然地想到大世界,依然重操旧业仍然唱滩簧吧。
她到以前的戏班子一看,原来的人马都没了,全是不熟悉的新人,班主也换了。没办法她只得去找小胡蝶。刚巧杜鹃也在,她是个侠义之人,笑着说:“看来解铃还需系铃人哪——是我害了你理该替你寻条出路。”她和小胡蝶商量后,问她:“你唱歌还行吧?”“行!我已往就是唱歌的。”“那再好都没有了。静安寺百乐门舞厅的乐队,要招歌女,你去试试怎么样?”“好,我去。”她马上答应。
他们在新雅饭店宴请百乐门乐队指挥刘琦,他见了方茹珍很高兴,说:“方小姐很漂亮,既然已往是唱戏的想必歌也唱得好,能否哼几句听听?”她想了想,清清嗓子唱了《四季歌》:“春季里来绿满窗,大姑娘漂泊到长江,江南江北风光好``````”刘琦边闭着眼睛听,边用手打着拍子。方茹珍唱完他连连摇头:“嗯,唱得不错,很有韵味,周璇唱得也不过如此。方小姐,我去年谱了一首歌,词也是我的,歌名叫《上海啊上海》。”说着从包里拿出一张歌纸交给她,“你回去哼一下,明天下午我去找你。请问府上是``````”
她怎能让他去那种破地方呢?马上说:“我那里不太方便。这样吧——明天还在这里,我请你吃饭。”“怎么美意思叫方小姐破费呢?”“那有啥?一顿饭我依然请得起的。刘先生,你的歌若使我出名的话,我感谢你都来不及呢!”“刘先生的大名,上海滩哪个不知谁个不晓?他写的歌一定会在上海唱红的。”“哪里,哪里?”刘琦嘴里虽虚心着,却乐得眉毛眼睛笑成一堆儿。
方茹珍是个急性子人,回到住处便把歌谱拿出来哼唱,一看调定的是F调,不由拖了拖舌头:“乖乖,音这么高,不要吃力煞的?”她自语一句后便试着唱起来,感到很动听,旋律也好,便认真练起来,练到晚上嗓子都有点毛了。
翌日晚上她按约定时间去了新雅饭店,不一会儿刘琦也来了。他听了她唱后夸奖说:“虽然嗓子有点哑,但唱得这么熟已属不易,证明你是下了功夫的,再把感情放出来那就更出色了。”“刘先生,调子能否定低点?”“不行,这歌就得F调,不然就没有这个味。这样吧,我用口琴给你伴奏,你再唱一遍。”说着他把口琴拿出来,“一定要唱出味道来。”
她唱完,他写意极了:“好,好!早晨我和白经理说好啦,月薪暂定三十块,点歌三七开,你得七成。怎么样,还可以吧?”她写意地点摇头:“谢谢刘先生。”他又通知她:“百乐门原有两个歌女,加上你一共三个,你是主唱,因为你的嗓音比她们高。另外,唱歌对你来说不是主要的,主要是跳舞。
方小姐,你陪客人跳得高兴,客人给的小费可全是你自己的,那要可观多了!”她这才晓畅其实自己只是个舞女。
这晚小胡蝶和杜鹃前去为方茹珍捧场,到百乐门舞厅前见门口悬着一块红绸横幅,上书:“重金礼聘香港闻名女高音歌唱家方小姐首次来本厅主唱。”
两人不由相视失笑:“哪来的香港歌唱家?”“哼,不怕吹破天!”她们走进舞厅,见方茹珍早在那里了,一身紧身的旗袍把身段勾勒得凹凸有致。白经理望着她眉花眼笑,称赞道:“方小姐的鲜艳盖过全厅所有的舞女和歌女,给本厅增光添彩啊!三十元月薪太少了,我决定再加你二十元,共五十元。”
方茹珍忙道谢:“谢谢白经理,谢谢白经理,我一定好好为您?力。”
方小姐一曲《上海啊上海》博得全堂彩,有人马上给她送上一只大花篮。在众人的要求下,她又唱了两首歌,《夜来香》和《茉莉花》,“哗——”掌声如轰鸣的浦江潮水。歌罢立即有好几位先生邀她跳舞,她礼貌地一一答应。舞会结束时,白经理摸出一张支票签了五十元,交给方茹珍:“先给方小姐五十元红钱。你要添置什么行头,尽管问账房间支取,我会看护他们的。”
这时有位歌女过来,求白经理说:“经理,我娘病了好些日子了,我想先支半个月工钿,给我妈去抓药``````”没等她把话讲完,白经理不耐烦地打断:“不是快到月底了吗?钱就一路拿了,叫你妈再耐些日子吧。”经理,我妈再不能耐了,昨晚她吐血了。”白经理依然不肯:“不到月底不能发钱,这是舞厅的端正。如果你失业在家找谁去要钱?就再耐几天吧,反正没多少日子了。”
方茹珍见了不由动了恻隐之心,从手提包里拿出十块钱塞给那歌女:“姐姐,你先拿去用吧。”“不,我怎么美意思拿你的钱呢?”她不肯接受。方茹珍又说:“姐姐。我们是一条船上的人,志同道合,分什么你我?依然快些拿了给你妈看病去吧,救大妈要紧。”听她这么说那歌女才收下了,感激地说:“等我妈病好啦,她会亲自来谢你的。妹妹,你歌唱得好,人更好。”
女侠除奸记(5)
方茹珍在百乐门舞厅唱红了,给白经理赚来大把大把的钱。这天她跟往常一样在台上演唱,正兴高采烈时,突然之间下面座位上站起一个人,怪声怪气地嚷:“姓方的臭娘,给我下来!”他这一喊扫了大家的兴,纷纷朝那里望去。只见那喊的人光着头,脸黑得像涂了层柏油。大家熟悉,他是静安寺地方的流氓,叫“黑皮阿三”。这家伙作奸犯科,谁在静安寺一带开店摆摊,月月要送他一份地藏钱,否则休想太平;舞女歌女也要孝敬他,不然休想站住脚;连叫化子小瘪三也要向他磕头尊他“老头子”,否则别想活命。因方茹珍进百乐门没去拜访他,今晚他便带了一帮小流氓寻衅来了。
方茹珍哪知这端正,以为由白经理挡着不会有事。舞厅里有小流氓捣蛋是司空见惯的,故她仍然唱她的歌。黑皮阿三见她不把自己放在眼里大怒,一声唿哨,两个小流氓便冲上台,扭住了方茹珍。
正在这危急关头,只听得一声断喝:“休得撒野!”伴伴随着声音,乐台上飞来一个女豪杰!你道是谁?她便是江湖上人称“檐上飞”的女侠杜鹃!只见她左右手一推,两个扭住方茹珍的小流氓便跌了个四脚朝天。她又身子蹲下腿一伸,将他们踢下台去。“好——”舞客们齐声喝彩。杜鹃一个鹞子翻身,稳稳地落在了舞池中心,手一指:“你们哪个不怕死的,敢跟姑奶奶比试比试?”黑皮阿三哪肯善罢甘休?见杜鹃身材只是常人,又是个美少女,便淫笑着:“嘿嘿嘿嘿,原来是个标致的妞。小的们,一路给我上啊!”那十几个小流氓便“嗷”地一声冲了已往。
他们哪里知道杜鹃站在舞池中心是有目的的,因为舞池地面滑,人稍不当心就要摔倒,她一个人对付多人就要便宜多了!面对围上来的十几个小流氓,她镇静自若,不慌不忙,拳脚并用,身子灵活,只听得“扑通扑通”,那些小流氓一个又一个倒了下去,摔得鼻青眼肿。
黑皮阿三知道吃了亏,手放到嘴里“嘘——”地一声长哨。小流氓们一蹶一拐地离了舞池。“哈哈哈哈``````”舞客们轰然大笑。黑皮阿三岂肯认输?指着杜鹃说:“小妞,这里不是施展我们本事的地方,你有种明天下午两点
到梵皇渡约翰大学旁的空地上,咱们好好较量教量。你敢来吗?”怎么不敢?到时一定奉陪!”杜鹃双手抱拳笑盈盈说。
黑皮阿三知道这女侠本领高强,恐怕自己不是她的对手,如败在她手里,
以后怎么在静安寺安身立脚?突然之间之间之间他想到自己的把兄弟“铁臂膀”阿贵,是
徐家汇地方的流氓头子,因用手臂挡击来的木棍木棍断裂,故得了个“铁臂膀”的名声,在徐家汇地区称霸。翌日一早他去阿贵那里,买去了好酒佳肴。
“兄弟,你有什么事要我帮忙?”阿贵问。“你怎么知道我有事找你?”阿三问。“这么些年我还不知道你的脾气?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快说——什么事?”阿三哭丧着脸把昨晚在百乐门舞厅失风的事道了出来,气恨地说:“这臭娘厉害得不得了,把我下面的十几个弟兄都打翻在地。”“那你干吗不上去?”阿贵问。“不瞒哥哥,我怕也不是她的对手,如果也被打翻在地,那我另有什么面子?”“听你这么说这娘们有点来历,咱可不能输给她。”“是啊,所以兄弟来找你,务需要置于她死地。”“好,一不做二不休,咱们把这娘们做了!”阿贵举手做了个劈的姿势。“哥哥,咱们不能明的来,要偷偷地,趁她不注意时`````”他们商量后,决定在杜鹃去梵皇渡的路上对她下手!
吃罢午饭两人便出发了。黑皮阿三的那些小喽?各带短家伙埋伏在约翰大学的附近,阿三对他们说:“看到我和阿贵动了手你们就一拥而上,把她往死里打,打死了我有重赏。”“嗳,嗳。”喽?们一个又一个低头弯腰答应。
再说那杜鹃,对上海不太熟悉,不知道梵皇渡在哪儿?一路上问讯而来,先到曹家渡再向西,看到梵皇渡的路牌知快到了,却不知那里埋藏着杀机!
她正行走着,背后突然之间之间之间窜出一人,凶猛朝她挥臂。杜鹃是何等武艺?听得脑后生风,身子一蹲,阿贵挥了个空,因用力过猛身子一倾。杜鹃揪住这机会,伸脚一勾,只听“叭哒”一声,阿贵跌了个嘴啃泥。杜鹃刚收住脚,见对面黑皮阿三穷凶极恶地朝自己扑来,她抖擞精神,使劲朝他下身踢去。“嗳?”一声,阿三捂着小腹跌出去一丈多远。这是杜鹃的绝招——踢千斤!阿三痛得在地上打滚。
那些小喽?,发一声喊全拥了上来。杜鹃绝不镇静,两臂左右开弓,双腿前踢后蹬,快如闪电,捷似流星。只见挨着她拳脚的人,纷纷像秋风扫落叶,霎时倒下了一片,剩下不多几个都躲避开去,唬得脸都泛了白,手里的家什都快捏不住了。
阿贵知道遇上了高人,忙大声喊:“兄弟们,快住手,我们遇上三圣母了!”他自己则单膝跪下:“小的们有眼不识泰山,多多得罪,请圣母高抬贵手,饶了我们吧。”见他认了输,杜鹃便收了拳脚,扔下一把铜钱:“给你们治伤去吧!”言罢转身扬长而去。
她怕黑皮阿三出气出在方茹珍身上,故翌日晚上又去了百乐门舞厅,幸好一晚上都很太平。散场时那个被方茹珍帮助的歌女来还钱,见她脸有泪痕,杜鹃问:“你哭什么?难道你妈妈的病没法治了?”她呜咽着说:“不是的,是经理找我谈话,算给了我月钱,却停了我的生意。”“为什么?”“白经理说现在有了方小姐,我是多余的。”“岂有此理!”杜鹃怒从胆边生,“走——找他去评理!”方茹珍一把拉住她:“明天这么晚就算了。姐姐,你明天晚上等在舞厅门口,我早点来,陪你一路去找白经理,一定会挽回的。”
那歌女摇摇头:“方小姐,谢谢你的美意。我看你也别在百乐门唱了,因我看见有几个小流氓在舞厅门口探头探脑,我熟悉是黑皮阿三的人,估计他们要来报复,因见女大侠在所以不敢轻举妄动。方小姐,你总不能让女大侠天天做你的保镖吧?你有这么好的一副嗓子,还怕在上海滩没地方吃饭?何必在一棵树上吊死呢?”
听她说得有理,杜鹃道:“方小姐,既然白经理无情,那你也无义,一走了事!再说我也不可能天天陪你,我闯了这么大的祸,黑皮阿三一定要来报复。俗话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我看你依然换个地方唱吧。”方茹珍却摇着头:“我方兴未艾,依然再唱一个时期吧,再说明晚我还要替这位姐姐说情呢,因为我才使姐姐丢了饭碗的。”“你倒也有点侠义心肠。”杜鹃夸奖说,便不再劝她了。
第二天晚上杜鹃又陪方小姐去了。方茹珍带着那歌女找到白经理,说:“经理,你解雇她不如解雇我,不能因为我叫她丢了饭碗,那样的话我只可以到别处去唱了。”白经理一听急了,因为方茹珍来百乐门不到三个月已唱红了半爿天,每晚舞客纷至沓来,连外滩那么远地方的人也赶了来,方茹珍是百乐门舞厅的摇钱树,他白经理能得罪她吗?再说旁边站着那武艺高强的女大侠,他更得罪不起!所以他爽快地答应:“那就看在方小姐的面子上留下她吧。”方茹珍笑着说:“那就谢谢白经理了。另外,今夜我要和她一路登台演唱。”白经理又卖她的面子一口答应。
他们正说着话,突然之间门房来报,说黑皮阿三同另外一个人前来拜访。他们来干吗?是善依然恶?杜鹃心里在问。一会儿他们出去了,和阿三同来的便是那个阿贵。“白经理,幸会,幸会!”他们双手抱拳,“不过明天我们找的是这位三圣母!”杜鹃挺身而出:“一人做事一人当,你们找我干吗?”“圣母,您误会了,明天我们是专程来赔罪的,另外还想知道你老是哪路仙人?日后也好去拜访您。”
杜鹃雄赳赳说:“我姓杜,我爹就是杜天龙。”阿三和阿贵大吃一惊:“原来是老前辈‘云里鹤’的千金,失礼,失礼!”他们忙施礼不迭,“杜老先生在江湖上是人人称道的英雄,难怪他千金也这么仗义,令人敬佩之极!”见他们心服口服,杜鹃趁机教训他们几句:“与人应该为善,不可作恶。俗话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为何不报,时辰未到。”“是,是,请圣母放心,小的们一定牢记在心。”她又说:“上海滩也有我许多朋友,如果你们敢为难方小姐,嘿嘿,休怪我不虚心——”“不敢,不敢。”他们摇首摆尾似巴儿狗。
不久杜鹃离开上海去了杭州,又干了几桩大张旗鼓的大事,那是后事,以后再叙。
北宋熙宁年间,东京开封出了个奇人,谁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都叫他“杨神瞎”。传说,杨神瞎年轻时为人耿直,见到不平之事,常常挺身而出,帮助弱者讨还公道。哪料, ..
1992年10月9日,西非国家几内亚比绍普拉亚国际机场,一位健壮的黑人小伙和一位东方女孩手牵手从一架法航国际航班走下舷梯,前来接机的亲友们围着两人跳起了舞,他们用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