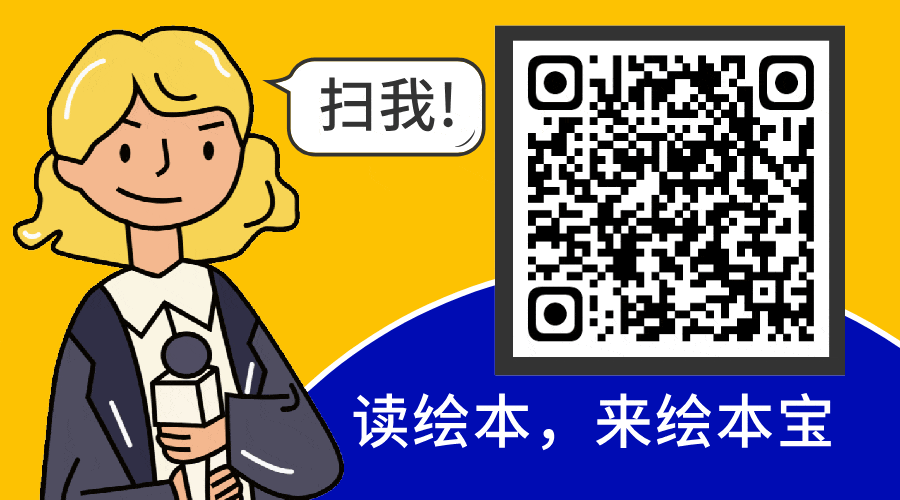

那耳喀索斯现在已经十六岁,介乎童子与成年人之间。许多青年和姑娘都爱慕他,他虽然风采翩翩,但是非常傲慢执拗,任何青年或姑娘都不能打动他的心。一次他正在追鹿入网,有一个爱说话的女仙,喜欢搭话的厄科,看见了他。厄科的脾气是在别人说话的时候她也一定要说,别人不说,她又决不先开口。
厄科这时候还具备人形,还不仅仅是一道声音。事先她虽然爱说话,但是她事先说话的方式和现在都没有什么不同——无作是听了别人一席话,她来重复前面几个字而已。这是朱诺干的事,因为她时常到山边去侦察丈夫是否和一些仙女在厮混,而厄科就故意缠住她,和她说一大串的话,结果让仙女们都逃跑了。朱诺看穿了这点过后,便对厄科说:“你那条舌头把我骗得好苦,我一定不让它再长篇大套地说话,我也不让你声音拖长。”结果,果然灵验。不过她听了别人的话以后,究竟还能重复最终几个字,把她听到的话照样归还。
她看见那耳喀索斯在野外里徜徉过后,爱情的火不觉在她心中燃起,就偷偷地跟在他前面。她愈是跟着他,愈离他近,她心中的火焰烧得便愈炽热,就像涂抹了易燃的硫磺的火把一样,一挨近火便燃着了。她这时真想接近他,向他倾吐软语和甜言!但是她天生不会先开口,本性给了她一种限制。但是在天性所许可的范围之内,她是预备等待他先说话,然后再用自己的话回答的。也是机会凑巧,这位青年和他的猎友正好走散了,因此他便喊道:“这儿可有人?”厄科回答说:“有人!”他吃了一惊,向四面看,又大声喊道: “来呀!”她也喊道:“来呀!”他向前面看一看,看不见有人来,便又喊道: “你为什么躲着我?”他听到那边也用同样的话回答。他立定脚步,回答的声音使他迷惑,他又喊道:“到这儿来,我们晤面吧。”没有比回答这句话更使厄科高兴的了,她也喊道:“我们见晤面吧。”为了言行一致,她就从树林(wood)中走出来,想要用臂膊拥抱她干思万想的人。然而他飞也似地逃跑了,一面跑一面说:“不要用手拥抱我!我宁可死,不愿让你占有我。”她只回答了一句:“你占有我!”她遭到拒绝过后,就躲进树林,把羞愧的脸藏在绿叶丛中,从此独自一人生活在山洞里。但是,她的情丝未断,尽管遭到弃绝,感觉悲伤,然而情意倒反而深厚起来了。她辗转不寐,以致形容消瘦,皮肉枯槁,皱纹累累,身体中的滋润一切化入太空,只剩下声音和骨胳,最终只剩下了声音,据说她的骨头化为顽石了。她藏身在林木之中,山坡上再也看不见她的踪影。但是人人得闻其声,因为她一身只剩下了声音。
那耳喀索斯就这样以儿戏的态度对待她。他还以同样的态度对待水上或山边的其他仙女:甚至这样对待男同伴。最终,有一个受他侮慢的青年,举手向天祷告说:“我愿他只爱自己,永远享受不到他所爱的东西!”涅墨西斯听见了他这合情公道的祷告。
附近有一片澄澈的水塘,池水晶莹,像白银一般,牧羊人或山边吃草的羊群牛群从来不到这里来。水平如镜,从来没有鸟兽落叶把它弄皱。池边长满青草,受到池水的滋润。池边也长了一片密林,遮住烈日。那耳喀索斯打猎疲倦了,或天气太热了,总到这里来歇息,他爱这地方的幽美,爱这一池清水。正当他昂首饮水满足口渴的欲望的时候,心里又滋长出另一种欲望。他在水里看见一个美须眉的个人形象,马上对他发生爱慕之情。他爱上了这个无体的空形,把一个影子当作了实体。他望着自己赞羡不已。他就这样目不转睛、分绝不动地谛视着影子,就像用帕洛斯的大理石雕刻的人像一样。他匍伏在地上,谛视着影子的眼睛,就像是照耀的双星;影子的头发配得上和酒神、目神媲美;影子的两颊是那样光芒,颈项像是象牙制成的,脸面更是光彩夺目,雪白之中透出红晕。总之,他自己的一切值得赞赏的特点,他都赞赏。不知不觉之中,他对自己发生了向往;他赞不绝口,但现实他所赞美的正是他自己;他一面追求,同时又被追求,他燃起爱情,又被爱情焚烧。不知多少次他想去吻池中幻影。多少次他伸手到水里想去拥抱他所见的人儿,但是他想要拥抱自己的企图没有成功。他不知道他所看见的东西究竟是什么,但是他看见的东西,他却如饥如渴地追求着。水中幻象现实在愚弄他,他却被它迷惑住。愚蠢的青年,一个瞬息即逝的幻象,你也想去捕获么?你所迫求的东西并不存在;你只须离开此地,你热爱的对象就消逝了。你所见到的只是形体的映影,它本身不是什么实体。它随你而来,随你而止,随你而去——只要你肯去。
他饭不吃,觉不睡,一向呆在池边,匍伏在绿荫草地上,一双眼睛死盯住池中假象,者也看不够,而丧生之祸,也正是这双眼睛惹出来的。他略略坐起,两手伸向周围的树木喊道:“树林啊,有谁曾像我这样苦恋过呢?你见过许多情侣到你林中来过,你应当知道。你活了几百岁,在已往漫长的岁月里,你可记得有人像我这样痛苦么?我爱一个人,我也看得见他,但是我所爱的,我看得见的,却得不到。爱这件东西真是令人迷惘。我最感难受的是我们之间既非远隔重洋,又非道途修阻,既无山岭又无紧闭的城关。我们之间只隔着薄薄一层池水。他本人也想我去拥抱他,因为每当我把嘴伸向澄澈的池水,他也抬起头想把口向我伸来。你以为你必然会接触到他,因为我们真是心领神会,当中险些没有隔阂。不管你是谁,请你出来吧!独一无二的青年,你为什么躲避我?当我险些摸着你的时候,你逃到什么地方去了呢?我想我的相貌,我的年龄,不致使你退避吧!许多仙子还受过我呢。你对我的态度很友好,使我抱有希望,因为只要我一贯你伸手,你也向我伸手,我笑,你也向我笑,我哭的时候,我也看见你眼中流泪。我向你摇头,你也摇头回答,我看见你那美好的嘴唇时启时闭,我猜想你是在和我答话,虽然我听不见你说什么。啊,原来他就是我呀!我晓畅了,原来他就是我的影子。我爱的是我自己,我自己引起爱情,自己折磨自己。我要怎么办呢?我依然站在自动方面呢,依然被动方面呢?但是我又何必自动求爱?我追求的东西,我已有了;但是愈有愈感缺乏。我若能和我自己的躯体合并多好啊!这话说起来很不像情人应该说的话,但是我真愿我所爱的不在眼前。我现在痛苦得都没有力气了;我活不长久了,正在青春年少,眼看就要绝命。死不足惧,死后就没有烦恼了。我愿我爱的人多活些日子,但是我们两人原是同心赞成,必然会同死的。”
他说完这番话过后,悲痛万分,又回首望着影子。眼泪击破了池水的平静,在波纹中影子又变得模糊了。他看见影子消逝,他喊道:“你跑到什么地方去呢?你这狠心的人,我求你不要走,不要离开爱你的人。我虽然摸你不着,至少让我能看得见你,使我不幸的爱情有所依靠。”他一面悲伤,一面把长袍的上端扯开,用苍白的手捶自己的胸膛,胸膛上微微泛出一层白色,就像苹果有时候半白半红那样,又像没有成熟的累累葡萄透出的浅紫颜色。一会儿池水平息,他看见了泛红的胸膛,他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就像黄蜡在温火前溶化那样,又像银霜在暖日下消逝那样,他受不了爱情的火焰的折磨,慢慢地要耗尽了。白中透红的颜色褪落了,精力消损了,怡人心目的丰采也消逝殆尽,甚至连厄科所热恋的躯体也都保存不多了。厄科看见他这模样,虽然心里还没有忘记前恨,但是很珍视他。每当这可怜的青年叹息说: “咳!”她也回答说:“咳!”凡当他捶打胸膛的时候,她也收回同样的痛苦的声音。他望着熟识的池水,说出最终一句话:“咳,青年,我的爱情落空了!”他的话又在这地方引起了回声。他说声“再见”,厄科也说:“再见”。他把疲倦的头沉在青草地上,死亡把浏览过自己主人丰姿的眼睛阖上了。他到了地府以后,依然不住地在斯堤克斯河水中照看自己的影子。他的姐妹们——奈阿斯——捶胸哀恸,剃掉头发,为她们的兄弟志哀。德律阿德斯也悲痛不已,厄科重复着她们的哭声。她们替他预备好火葬的柴堆、劈好的火把和灵床。但是到处找不到他的尸体。她们没有找着尸首,却找到了一朵花,花心是黄的,周围有白色的花瓣。
(杨周翰 译)
从这里,许门飞过无边的天空,他穿着橘红色的外衣,飞到喀孔涅斯人当中,听见俄耳甫斯的声音在召唤他。但是俄耳甫斯召唤又有什么用处?不错,婚姻之神许门在俄耳甫斯 ..
这件事发生在山边,地下淌满了许多野兽的血,这时候正当中午,人影缩短,太阳和东、西的距离正好相等。年轻的阿克泰翁和猎友们正在荒野中前进,他和善地对他们说:“ ..